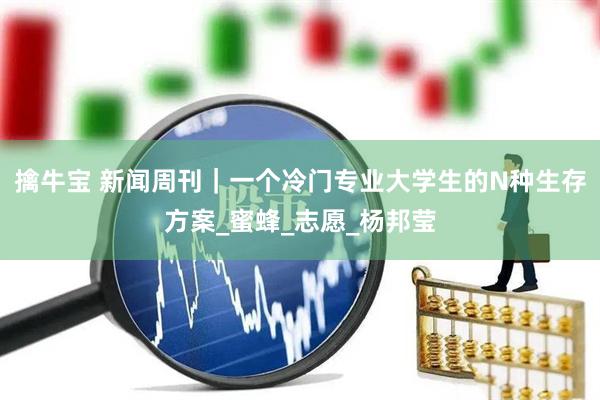
如何优雅地打开一只蜂箱而不被蜜蜂蜇?擒牛宝
首先,开箱前你要确保身上无异味(例如香水味,浓郁的身体乳味);其次,你可以用蜂蜡搓一下即将用于开箱的工具以及手;最后,开箱时切记动作轻快迅速,不要站在蜂巢口——专业术语为“蜂路”上,为蜜蜂通行让出通道。
这个答案来自一名云南农业大学蜂学专业大三在读学生。她叫杨邦莹,云南德宏人,今年22岁。3个月前,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与蜜蜂相关的问题后,她兴致勃勃点开评论框,熟练地写下了自己在实践中总结的开箱经验。
没人听说过蜂学专业吗?面对网友对她自报专业后的惊叹,她习以为常,也觉得有趣。近两年来,她活跃在社交平台各个与蜜蜂相关帖子的评论区,一遍遍不厌其烦地为陌生人做解释和科普。
蜂学专业的确足够冷门、小众。据公开信息,目前全国仅两所高等院校开设蜂学本科专业——福建农林大学和云南农业大学,每年招生规模约150人。
和很多调剂来的同学不同,最初,这个专业是杨邦莹自己选的。经过3年的学习,她对蜂学的兴致非但没有消退,反而愈加浓厚。只是,随着毕业进入倒计时,她要开始思考出路的问题了。
展开剩余92%未来何去何从?在理想和现实的拉锯中,她犹豫不决,甚至,“特别恐惧”。关于这个问题,除了自己,没人能给出答案。
开箱时穿的防护服。(受访者供图)
天生动物爱好者
复盘最初选专业的过程,一些非理性因素发挥了作用。
2022年高考结束后,杨邦莹发现自己的成绩只够上二本,失望至极,她不愿正视填报志愿这件事。眼看距离志愿确认截止日期越来越近,女儿迟迟不行动,妈妈着急了,威胁她,“如果你全权交给我选择,我就给你报去偏远地区读书。”
她被妈妈的话吓到了,报志愿这件事变成了仓促之下的紧迫任务。她这才开始认真思考:
首先不想出省;数学和物理学得不好要避开;对生命科学、自然生灵感兴趣;云南农业大学正因一个叫丁习功的学生发布的短视频火爆网络……然后,她看到了蜂学专业这个选项,一下子有了目标。
她猜想兴趣的源头也许和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。在云南,养蜂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。她记得,小时候爸爸和姨父都在养蜂,用的是传统的土蜂桶——将枯死的树干,挖空树芯制成。蜂桶吊在树上,成群的蜜蜂就会自己飞来。
“那些小蜜蜂,胖胖的很可爱。”童年经历让她对蜜蜂的印象只有亲切、喜欢,毫无恐惧。
她又猜想,或许,这种对动物的喜爱是天生的。她从小就拥有丰富的动物饲养经验:一对黄白相间的仓鼠,一只蓝眼睛的中华田园犬,一只小斑鸠,一只猫,一只鸽子。连电动车钥匙扣上的一只玩偶小狗也是她的宠物,被她唤作“多多”。
她将这种天性归因于自己的成长环境。“小地方出来的孩子,天然对土地、生灵、生命有亲近感。”
越这样想,学蜂学的意愿越强烈。为了提高被录取率,除了云南农业大学——她打破了不出省的原则——她将福建农林大学的蜂学专业也纳入了志愿填报表里。
虽然让出了志愿填报权,但父母对她也有不同的期待,“觉得女生读师范类专业比较合适”,她对此兴致索然。家族中有一位上过大学的小姨可以成为一个合适的咨询对象,但在那个时候,她突然生出了一种“叛逆心”,“听了他们这么多年话了,我自己要选一次专业”。她压根没有把志愿填报表拿给小姨看。
至于高考志愿咨询服务,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。她至今对张雪峰这个名字感到陌生,“没有看过他的直播”。在强烈的兴趣面前,所有客观冷静的分析与建议都魅力尽失。
于是,那个重要的时刻,她自作主张在志愿填报页面点击了提交。就这样,她成为云南农业大学蜂学专业2022级录取的21人之一。
她是天生的动物爱好者。(受访者供图)
蜂的世界
蜂学不是单纯研究如何养蜜蜂的。进入大学后,一个广阔的关于蜜蜂的世界向她打开了,那是一个可以走得很深很远的世界。
原来蜜蜂是红色色盲,而植物界很少开红色的花,所以小学生绘画习作上,蜜蜂围着红色花朵采蜜的场景在现实世界并不常见;东方蜜蜂对抗天敌——胡蜂的手段是,利用其耐热性更低的弱点,围上去将其层层叠叠包裹起来,活活热死;蜜蜂不是逢蜜便采的,它不喜欢芒果花,要想让蜜蜂为芒果花授粉,需要特别训练;短视频平台上,号称“俄罗斯蜂王浆”的产品销售火爆,“其实中国是蜂王浆出口最多的国家”,她一眼识破。
3年的学习生活,她享受其中,为每一次知识的更新惊喜。
有一年假期回家,她听到姨父说起,有个人可以培养蜂王,很厉害。她在心里暗想,这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,只不过他们没有学习过,“要是我的话,我也可以弄出来。”
这是她眼中传统养蜂人和蜂学专业科班生的区别:“他们更多是通过经验判断现象擒牛宝,然后想一些解决方法,我会用学习的知识去系统分析,就比他们更全面、更专业一点,也少走一些弯路。”
最吸引她的还是实践的部分。一门关于蜜蜂饲养管理的课程,考核要求是,在一年的时间里,养活一群蜜蜂。她因此有机会亲身体验蜂的四季。
要特别留意春天。刚刚度过越冬期的蜜蜂还比较脆弱,云南多倒春寒,骤降的气温对蜜蜂来说是致命的。
早春时节,大自然里大多数植物还没有开花流蜜,正值春繁期,蜂巢里还有很多小幼虫等待被喂养,所以养蜂人要用糖水和蜂花粉为蜜蜂制作饲料。她查阅文献,学着别人的样子配制好饲料,一条一条黏在巢框上。
在夏天,开箱会变成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。
在大学里学养蜂,用的是朗氏十框蜂箱,长50厘米,宽30厘米,高25厘米,一箱可以装进“一群”蜜蜂,大约两万多只。为了观察蜜蜂的生存状态、及时清理蜂巢、补充饲料,常常需要打开蜂箱检查,这个步骤就被称为开箱。
考虑到天热,穿多了行动也不方便,她常常简化开箱时的必要防护措施,只穿着半身的防护衣,下半身露出光腿来,因此,腿部成为遭遇蜜蜂攻击的重灾区,最惨的一次,被蜇了5针。
被蜜蜂蜇了很痛,起初四五天后红肿才会消退,但蜇着蜇着,杨邦莹发现自己恢复得越来越快,只是涂抹最常见的丹皮酚软膏,一两天后红肿就消失了。身体在适应这份工作。
对于蜜蜂,她从来没有产生过恐惧。阳光下暴晒的辛苦,来回搬运蜂箱的辛苦,365天悉心照顾一群小动物的辛苦,皮肉之苦,她都不觉得是苦。
“看看那些蜜蜂的体色和形态,它们被我养得胖胖的,真的觉得它们很可爱,也就没有那么累了。”她说,“亲自去做这些事情,最后的结果和我预期中一样,就会很有成就感。”
取蜂毒。(受访者供图)
在学校养的蜂。(受访者供图)
寻路之难
说不清到底是在哪个时刻,这些快乐的学习体验中掺杂了焦虑。
大三那年,去一家生产蓝莓和草莓的农业公司实习时,她看到工厂里的蜂箱被随意摆放,“感觉饲养管理上没有那么好”;另一方面,她注意到这家企业实际上是通过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提高产量,于是疑心,“老师上课时讲的,蜜蜂授粉可以提高产量,那为什么在实际生产中,这么多种植基地却不重视呢?究竟哪种手段对产量提升更有效?”
她继而想到,也许以当前全社会的认知状况来说,蜂学的受重视程度都没有那么高,“人们的认知仍停留在蜂产品上”。
第一次对就业前景产生强烈的担忧,是与往届毕业生交流过后,她发觉哪里不对劲。“大家读这个专业,大部分人要么考公务员,要么考事业编,或者转行,很少有留在蜜蜂行业的。”
那些留下来的呢?
她听闻,一位5年前毕业的师姐,在蜂产品相关企业做了1年的仓库管理后,离职报考了研究生。其他选择进入蜂产品加工企业的人,大多进入了车间流水线,或者从事销售岗,薪资待遇低、工作内容枯燥。
但若以基础岗位进入企业后,能否有明朗的晋升路径呢?她知之甚少,承认自己“跟社会有点脱节”。
行业内也有技术含量更高一些的工作,例如训练蜜蜂授粉。老师建议,要去其他省份(青海、广西等)寻找就业机会,那里有规模更大的种植基地。对于远离家乡谋生,她心存顾虑。
盘点过后,她发现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,她既梦想继续留在蜜蜂行业,也期待着一份可观的收入。
她曾有过一些热血而天真的想象。
大一时,她参加过学校举办的学业规划大赛,获得了校级优秀奖。在规划目标上,她写着:未来要创业开一家跨国蜂业公司,不局限于蜂产品,还要开发蜂产品相关的化妆品、蜂针医疗的业务。
作为创业筹备步骤,她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马兰花创业培训,通过了考试,拿到了证书,计划着,未来“如果地方上有扶持创业的政策,可以持证去申请无息贷款”。
不需要在现实中碰壁,创业的激情和野心很快被她扑灭。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,也许是感受到,近几年父亲生意失意的压力投射在了家庭氛围里,她看到了理想背后的现实性:“我的家庭无法承受创业失败的后果。”
正在进行脱花粉的实验。(受访者供图)
被“嫌弃”的专业
继续深造,是她当前的优选项之一。只是,距离2026年考研还有5个多月,到底报考哪个专业,她仍在纠结。
在科研领域,关于蜜蜂,有过很多有趣的发现。
100年前,德国动物学家、行为生态学创始人弗里希发现,采集蜂在回巢时,通过以“8字舞”的方式运动,向其他蜜蜂传递蜜源的消息。1973年,弗里希因为一系列有关蜜蜂“舞蹈语言”的发现,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50年后,61岁的中国学者谭垦及其团队在《科学》发表了一篇论文,再次更新这一发现,也颠覆了全球学界认知:采集蜂在回巢时以“8字舞”的方式进行信息沟通并不是蜜蜂与生俱来的本能,蜜蜂语言也受到“言传身教”的影响,这揭示了,相互交流和学习是蜜蜂社会取得成功的基石。
这一发现让国内蜂学界振奋不已,杨邦莹是受到激励的学生之一。那一年她读大一。学院里一位老师和谭垦相识,邀请他来学校做过一场线下讲座,与学界前沿人物的近距离接触,让她心生一种大胆设想:或许,也可以走一条科研之路。
蜂学属于小众学科,目前,专业研究者较少,学术领域仍留有大量空白。
她记得老师上课时讲过蜂群衰竭失调(简称CCD,又称蜂群崩溃综合征),指的是一种工蜂突然大规模消失的现象。究竟是因为农药,还是蜂螨寄生?学界猜测很多,但至今仍无定论。
在蜜蜂的世界,诸如此类的未解之谜无穷无尽,谁能成为下一个揭秘者?她头脑中有无穷的想象。
蜂学对应的硕士研究生专业叫作特种经济动物饲养,她很感兴趣。摆在前面的是另一个关键问题:究竟要不要继续研究蜜蜂?
压力主要来自家庭。出于对未来就业前景的担忧,父母希望她转行,“读研究生可以,但蜂学不支持你读。”她尝试沟通了几次,次次都发生冲突。见父母态度坚决,她“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”。
她理解父母。“我爸爸害怕我做这个工作,一个人东跑西跑,心疼我吧。”她同时留意到今年有相关政策提到,“未来可能要大力发展畜牧业”,那或许意味着,这个领域将来会有更多就业机会。作为一种折中方案,她考虑将畜牧业作为自己的考研方向。
可是真的要放弃蜂学了吗?她觉得可惜。她懂养蜂,也懂其他。她懂蜜蜂的生理特性、行为,懂它们的饲养管理,懂蜂产品,懂蜜蜂在作物授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,还对蜜蜂应用于人类医疗的可能性充满了兴趣。
“不是为了应付考试,是真的感兴趣,认真地学了。”她说。
杨邦莹(受访者供图)
野生的蜂
她曾质疑过上大学的意义。“难道大学只是为了让我们有书读,有一个本科毕业证吗?”她有些丧气地说。
但讨论最初选专业的过程时,她又立刻说:“我其实不后悔。”
“如果再来一次,我还是会选择这个专业。选其他专业毕业也会遇到问题,还不如选个喜欢的呢。”她说。
考研不行就回家考公。
听说明年有单位开设了新的岗位,专招蜂学专业毕业生,也可以去试试。
以前有家大企业专门来学校定向招聘,把蜂学专业学生都招走了。这种机会也是有的。
再不行,就去附近的大型养殖场养小猪,专业对口,培训一下就能上岗,薪资待遇不错。往届毕业生里也有成功案例,曾有一位师哥在养殖场干到了厂长的位置。
她向我一一梳理这些选项,然后发现,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令人心生恐惧的未来,“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”。
她那么了解蜂,但在她的视野里,仍有一处盲区:那些野生的蜜蜂是怎样生存的呢?
它们会自己找地方筑巢,会自发进行新老交替,一个成熟的群体里,总有一些生存下来,一些死掉,但生生不息。
它们会自己想办法度过春夏秋冬。在冬天到来的时候,无处采蜜的时候,幼虫亟需哺育的时候,也许,它们会迁徙。
(半岛全媒体记者 牛晓芳)擒牛宝
发布于:山东省简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